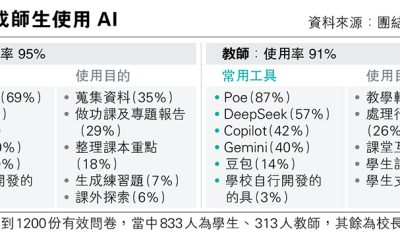副刊
吾生有杏:培訓未來醫生

【明報專訊】小時候,我眼中的醫生大多都是高高在上,有些醫生像包公(黑口黑面),有些像二郎神(天眼生在額上,看不見凡人)。有好醫生嗎?當然有。但黎民百姓總是「只要信,不要問」,不可質疑,例如手術永遠都是成功的,失敗的只是病人。
在我學醫的年代,醫生的個性很強,主導力也很高。那個年頭,某某醫院、某某部門或某大國手往往影響了醫療發展的方向及意識形態。「師徒制」便成為了訓練人才的主流思想,當時的年輕醫生很強調他們師承何處,有的彷彿以為自己是少林武當名門大派弟子,亦有被視為明教的異教徒。總之各師各法,百花齊放,當然亦少不免有正邪對立的局面。
當年我學藝於一所位於新界偏遠從填海得來(圓洲角)的新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我的師父(沈祖堯)雖是年輕有為,可是當年缺乏江湖地位。可想而知,那些年並不容易。但師徒制讓我認識什麼是生命影響生命、以人為本及力爭上游。幾十年間,我們亦栽培了不少本地及海內外的人才。
如今我們身處於醫療企業管治的大一統年代,為了保證質素、提升效率及控制成本,企業管治是無可避免。可是在這意識形態下,追隨從上級發出的指引比模仿師父更重要。醫生整體質素或有所提升,但個人面目卻變得模糊不清,彷彿全都是生產線上有保證的成品。當醫生與病人關係變得疏離,醫生逐漸變成了醫療服務提供者(health services provider),當服務承諾出現落差,投訴及訴訟便隨之而來。我們再不能用愛心與信任彌補病人肉體及心靈上的傷痛。
更需學醫治病人心靈
展望將來,我慶幸香港特區政府決定投放龐大資源培訓更多醫生,而AI的大時代勢必將醫療水平推上另一層次,令更多病人受惠。但我們更應反思,如何培育能夠應對未來的醫生(future-ready doctors)?人工智能或會彌補醫生的經驗不足或主觀判斷失誤,達到精準醫療的美滿成效。但假若醫生只懂得操作及分析新科技,我們又會否淪落為「醫療AI技師」?
儘管有一天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發展成為具有類似人類的智慧(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取代我們執行醫療工作;但請記着:科技或可精準醫病,唯獨仁心才能真正醫人。未來的醫生更需要學習醫治病人的心靈。
文:陳家亮(腸胃肝臟科專科醫生)
(中大醫學院教授,教學生、醫病人、做研究,親筆分享杏林大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