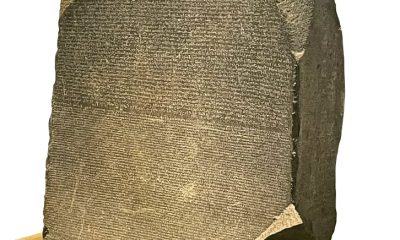副刊
堅持到老達人 鄭鎮炎 有興趣就不覺難 74歲重走6000公里長征路

【明報專訊】1934年10月,紅軍面臨被國民黨圍剿殲滅的絕境,迫不得已放棄中央根據地,進行戰略轉移,沿途一邊突破國民黨的圍追堵截,一邊攀山越嶺,經過江西、福建、貴州、雲南、四川等10多個省份,1年後成功到達陝北吳起鎮重整勢力,後稱二萬五千里長征。90年後,年屆74歲的香港人鄭鎮炎獨自花近一年時間重走這6000多公里長征路,在此之前,他還完成了英格蘭總長約300公里的Coast to Coast山徑、西班牙的朝聖之路,以及總長約170公里、總爬升約1萬米的環白朗峰。
地形變化大 難完全復刻路線
「總共走了250天,6096公里。」鄭鎮炎2024年10月17日在江西渝都起行,這次他儘量復刻紅軍的出發和結束日子,但就無法完全「重走」紅軍當年的實際路線。「當年紅軍的路線是走山徑,因為紅軍打仗很多時候只能走山徑,但(現在)很難找得到的,因為地形有很大變化。」90年前紅軍為避開國軍看守的主要幹道,在險要惡劣的山脈之間穿梭,爬4000多米的高山、過沼澤地、爬雪山。「這些都是自然條件非常艱難的地方,紅軍過這些地方是死了很多人的。那時沒有路,加上如果遇上大雪,如果食物不夠、衣著不夠,還有很多紅軍是南方的士兵,他們不一定會適應高原的氣候。」考慮到難以考究實際路線,以及獨遊的安全問題,鄭鎮炎沒有走山徑,選擇走馬路、行人路,每天背着約15公斤的背包,步行25至30公里,「但基本上是紅軍走過的城鎮,有紀錄的我都盡量去走」。
中國政府近年提倡發展紅色旅遊,鄭鎮炎訪問時也送給記者一份印刷精美,簡述紅軍長征路線、經過城鎮和重要故事的長征地圖。這次他的旅程也花了不少時間參觀政府整修的遺蹟和紀念館,「因為沿途發生了很多的戰鬥,有些地方政府會建一個紀念館,介紹長征的歷史和文物,那個地方發生的戰鬥,或者是開會做了什麼決定,比如『四渡赤水』 、『會理會議』、『金沙江』等 」。因為香港人的身分,這次他重走長征路的旅程亦獲大公報、內地媒體廣泛報道。
70年代「中國熱」
讀《紅星照耀中國》埋下種子
為什麼這個香港人會對紅軍長征有興趣?「我在1972年入大學」,1972年是中美關係破冰的重要分水嶺,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是1949年以來首位到訪中國大陸的美國在任總統,「當時適逢中美開始接觸,全世界都掀起一個中國熱。我當時剛入大學,在大學書店買了一本書Red Star Over China(《紅星照耀中國》),是一個美國記者Edgar Snow愛德加史諾寫的 。」《紅星照耀中國》記錄1936年,史諾深入當時的共產黨根據地,先後採訪了周恩來、毛澤東、彭德懷等人,與紅軍同吃共住4個月。當時紅軍剛完成長征,正處於調整和發展的階段。
「這本書記述了長征的歷史,還有當時紅區的社會風貌。雖然物質非常貧困,但是人們的精神呈現一片很蒸蒸日上的精神風貌,人們很團結、友愛、平等、民主,呈現了一種很理想的社會模式。」例如史諾提到高層領導人與普通士兵和群眾在物質待遇上幾乎沒有區別,大家吃一樣的食物如小米和蔬菜,穿一樣的軍裝;也記載了紅軍與當地農民關係良好,紅軍嚴守紀律、絕不容許貪污腐敗,並積極教育民衆識字。史諾看見的共產黨,是尚在增加支持者、擴大勢力的革命早期,《紅星照耀中國》打破國民黨封鎖,第一次向外界和西方全面地介紹中國共產黨的資訊。鄭鎮炎在1972年的香港閱讀,仍對書中描述的平等、理想化、為共同目標奮鬥的紅區生活和長征故事感到嚮往,「這本書可以說是我對國家認識的啟蒙,它播下了我今天走長征路的一些種子」。
「後來為什麼會走到長征,就是10幾年前看了一本書叫《兩個人的長征》,是兩個英國人所寫。這兩個英國人在北京教書,三四十歲左右,他們在一些中國人的幫助之下重走長征路。我看了書,覺得兩個英國人都可以走這個長征路,這樣是不是有一天我都可以走呢?」但當時鄭鎮炎還在工作、未退休,沒有時間,亦意識到這樣徒步一年、靠自己補給不容易。「但就覺得有朝一日,如果我退休有時間的話,如果有機會我真的很想走這個長征路。」這個目標一直掛在他的心上,直到他退休後,成功徒步完成歐洲幾條山徑、由成都徒步到拉薩,他信心大增,就着手準備這次長征之旅。
癡迷長跑、行山、徒步 運動難在堅持
這次超過6000公里的長征是鄭鎮炎最長距離的徒步旅程,但不是第一次。早在1996年,鄭鎮炎已經試過獨自徒步走過縱貫美國東岸的Appalachian Trail,「我一個人走了1000公里,走了45天。這是相當難走的,因為那些路是行山徑,不是馬路,山徑是凹凸、高高低低的。而且一個人走自己要帶食物,帶睡袋帶營」。30多年前,長距離徒步在香港仍不算太流行,更何况遠到美國行山,「這是因為我喜歡去書局看書,跟運動有關的書。我看了一本書叫Blind Courage,是一個盲人寫的。他就走了這個山徑,有一隻拉布拉多導盲犬帶着他走。山徑其實全長是3600公里,我只是走了三分之一左右。他走完之後,我覺得盲人都可以走,我開眼的,為什麼不行呢?」當時他剛好轉工作,就跟老闆說遲2個月、行完山才上班。
「還有1987年,我去美國參加一個10天的Outward Bound課程(外展訓練),這個課程是有關Mountaineering(攀山),還有Rope Climbing(攀崖)。」當年課程索價幾千美元,參加者一行10人中,只有鄭鎮炎一個亞洲人。「最記得第2天,7點開始行,全日都在緬因州的森林裏穿梭,密密麻麻的大雨沒有停過,走到晚上12點才找到露營的地方。而且在叢林裏面行,經常爬高爬低,下大雨就全部路都是泥濘,大家都走到筋疲力盡。紮好營地,一躺下就睡着了,累到什麼都不記得,第2天早上6點又起來行山。」他回憶當時同行的一位美國人參過軍打過越戰,說連打越戰都沒有這個訓練辛苦。其他人走到大罵髒話,質疑為什麼走這條路、領隊是不是帶錯路,但鄭鎮炎沒有出聲質疑,繼續默默地走。「我覺得你中國人去到那邊,你不能夠示弱、不能抱怨,沒有什麼好埋怨的,你自己報名、你自己付錢,沒有人叫你參加,你唯有咬緊牙關去挺過來。」
鄭鎮炎說自己最大的興趣就是運動,包括長跑、行山、徒步。香港1979年開始舉辦環水塘跑的水塘杯比賽,他全部水塘都跑過;在渣打馬拉松成立前,他就參加了石崗的香港馬拉松,至今完成了30多次馬拉松;1980年在法國留學時完成了3次100公里長跑。近10年他每星期都會行兩次山,每次4至6小時,他笑說香港的山應該都行得七七八八。67歲時登上非洲最高峰乞力馬札羅峰(5895米),之後完成哈薩克斯坦60公里越野馬拉松、尼泊爾60公里越野馬拉松。「因為喜歡那種挑戰,你喜愛運動,你要接受一種挑戰,挑戰你的體能,挑戰你的意志。你有興趣就……其實我不覺得有什麼難的。」
克服外在環境影響
報名不難、開始運動不難,最難的是堅持鍛煉、堅持繼續挑戰自己的心態,並堅持到老。鄭鎮炎說很多人問他重走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難不難,他說其實不難,每天走25至30公里,很多人都可以,不需要什麼特別訓練,只要有健康的身體就可以走。「但是」,鄭鎮炎說,「你每天不停地走的持續性是最難。你要堅持、堅持再堅持。不同的天氣、不同的心情,你都是不斷堅持,難是難在這裏。」回想250天的旅程,他說貴州那段路最具挑戰性,貴州天氣陰晴不定,遇上天陰下雨又寒冷,一起牀氣溫零下兩三度、天空灰暗潮濕,但徒步的人不同天氣都仍然要出發,他走在濕滑的路上也會鬱悶得問自己「為什麼要走這條路」。但多年運動磨練他,要克服外在環境對自己的影響,對自己有信心,「運動、長跑、行山,其實培養了我一種自律。例如這個星期我要跑20公里,如果我完成了,就代表我能夠控制到自己」。
退休徒步歐洲4大行山徑
「年齡不應是障礙」
5年前鄭鎮炎退休時碰巧是疫情,解封後他就打算到外國山徑徒步鍛煉一下,也為長征作準備。「我就去書局買了一本書 《世界十大行山徑》,我選了4條行山徑,一個是蘇格蘭的西高山,一個就是英格蘭的Coast to Coast,一個就是西班牙的Camino de Santiago(朝聖之路),另一個就是法國意大利瑞士的Tour du Mont Blanc(環白朗峰)。4條山徑加起來是1500公里,一共走了71天。」出發時他71歲,在整個歐洲徒步之旅,環顧所有徒步者,他是極少數的年老面孔。「可能71歲很多人什麼都不敢做了,但我不是太在意我的年紀,我在意的是我能不能做到一件事。」他從不覺得自己的年齡是障礙,「我覺得不是一個障礙,或者不應該是一個障礙。如果你覺得你做到這件事情,什麼年紀都沒有關係。但是你不可能說,『我這麼大,我就什麼都不去做』,我覺得是不應該的」。
他現在74歲,身體狀態仍然不錯,沒有俗稱「三高」的高血壓、高血脂和高血糖,也沒有長期病患。「我發覺我現在雖然74歲,但是唯一跟以前分別,就是做事情慢了一點,但是以前做的事情我現在都做到的。唯一就是慢慢來,就不會那麼容易受傷 。」其他人聽到他這個年紀仍在背着大背囊行山,或會勸喻他不要冒險,「我不是太在意別人的看法」。他說多年長距離徒步培養他獨自面對挑戰、特立獨行的力量。最清楚自己的能力和身體狀况、最明白這個追求這個目標有什麼意義的人是自己,「如果在意別人的看法,你是什麼都不用做,因為大家站的立足點不同,可能他自己有慢性病,但我沒有,我感覺很好。I’m feeling good, always feeling good」。
完成歐洲山徑徒步後,他的目標回到1972年時所播下的種子——二萬五千里長征。他還寫了一本書,書中他引用了美國作家烏爾曼(Samuel Ullman)詠青春的一首詩,開首便是「Youth is not a time of life, it is a state of mind.(青春不是年華,而是心態)」。他說尤其喜歡一句「Nobody grows old merely by a number of years. We grow old by deserting our ideals.(年歲有加,並非垂老;理想丟棄,方墮暮年)」。
文˙ 朱琳琳
{ 圖 } 黃志東、受訪者提供
{ 美術 } 朱勁培
{ 編輯 } 梁曉菲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