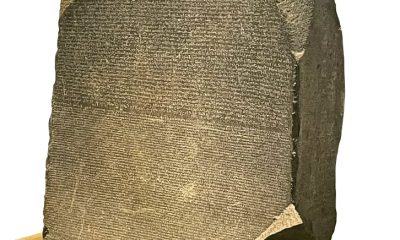副刊
主題旅遊:琴澳和鳴——橫琴邊界景觀札記

【明報專訊】月中筆者前往澳門欣賞十五運乒乓球賽。在兩場賽事的間隙,我打算充分利用這個時間,前往與澳門一水之隔,最近離氹仔島不到200米的珠海橫琴島進行一次「城市散步學」的小調研,觀察此島的城市人文景觀,以及大灣區語境下琴澳雙城融合與邊界再造之間的張力。對此,我借用了人文地理學中的「邊界景觀」(borderscape)概念去幫助思考。
思考「邊界」
邊界,代表着區隔、邊緣、差異、混雜,既由物質性存在的邊境實體如禁區鐵絲網、關口基礎設施等人工物維持,又依賴法律政策、文化符號表徵等隱形限制而存在。邊界景觀這一概念隨着全球化的跨國流動及人文地理與邊界研究中的「過程轉向」(processual turn)出現,使邊界得以被視為動態的社會過程和空間差異化的實踐。同時,此概念亦可轉化為動詞的「邊界景觀化」(borderscaping)去觀察具體的跨境經驗和與邊境相關的實踐。最後,「景觀」一詞延續了社會學家Appadurai的全球化五大景觀的討論,以可見性(visibility)去助我們思考邊界的表徵和美學及背後的政治,以及幫助香港人更好地自我反思同為灣區共融下的一員,認識邊界的豐富意涵。
特區化實踐
隨着1元車資的公交車通過橫琴大橋進入橫琴島,毋須任何特別通行證即可順利進入這個經濟特區。據官方文件稱,自2024年3月1日起,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正式實施分綫管理封關運行。進入橫琴的邊界被視為「一線」,受影響的是貨物而非人員。入島的內地貨物被視為出口,澳門貨物則可免稅進入橫琴。而離開橫琴島則視為「二線」,採取關口隨機抽檢方式管控人員與免稅貨物進出。我多次經由公交嘗試體驗出島的檢查均未達到目的,但「中國海關」的周總理手書,以及排隊通過關卡的體驗,則讓我想起幼時坐國內長途巴士入境深圳必經的特區關卡。深港人常說的「關外-關內」的特區「二線關」分界帶來的城市經濟人文景觀與規劃差異,即使在關卡早已廢除後仍持續到現在。這讓我開始憧憬和思考這條橫琴邊界,能否帶來相似效果。將地方特區化的規劃實踐,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政治哲學之一,而如今國內愈來愈多特區——天津自貿區、雄安新區、深圳前海特區、即將「封關」的海南自由貿易港區等。自上而下的特區化實踐並非一定能達到其預設的效果,也受各種區位因素的影響。
過橋後映入眼簾的,是中高檔的住宅公寓群、舒適宜人的海濱公園濕地,以及拔地而起的高技派現代主義(high-tech modernism architecture)寫字樓集群建築:與水文綠地交錯的玻璃帷幕、鋼鐵和鋁、流線造型成為此地的都市肌理(urban grain)特徵,頗有未來花園城市的感覺。一路上都能遇到壯觀的國際建築獎項大作——以橫琴山水為靈感的橫琴文化藝術中心、由以動感流線聞名的Aedas建築事務所建造的橫琴創新方,以及呼應島名形如橫臥琵琶古琴的珠海未來新地標天沐琴台。行經美麗的花海長廊,一路上都能聽到來自北方或西南地區的遊客的普通話口音,彰顯合作區以文旅觀光為核心的成果。
展示琴澳互通
在島的東邊,是澳門大學的橫琴主校區,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澳門特區政府管轄,須經由澳門本島方可進入且毋須過關,離開須到附近的橫琴口岸「回」到橫琴島,是個十分有趣的「一島兩制」邊界景觀。如今在橫琴島的西南端,新的澳大深合區校區也在建設當中,究竟未來會產生何種新鮮的跨境體驗,拭目以待。
隨後,我步入位於天沐琴台河心島內的合作區規劃展覽館,嘗試了解官方如何敘事建構和宣傳此島。在簡單挪用考古學知識與古地圖證明橫琴島與澳門的一衣帶水歷史聯繫,到社會主義時期的圍墾造田、戍邊衛疆的國家敘事後,場館主要展示合作區的形成歷程與發展現狀。部分基本以官方規劃文件、琴澳合作的媒介事件的照片和紀念物,以及現有合作區企業的成果展示。而琴澳兩地居民的跨境生命故事,則以出入證件和兩地商貿流通的物品作為證言,為兩地的合作互通提供民間經驗的合法性證據。
繼續沿城市中心水道天沐河騎車前行,路旁的宣傳標語與一些細節和景觀裝置引起我的注意。首先是幾條主幹道的名字——港澳大道、濠江路、香江路,隱約向遊人和投資者強調這裏的特區屬性。此外,繁體字標識不時出現在島上:充電樁標識、某些店名,或澳牌車等,在微觀層面隱約浮現出邊界的操演性(performative)呈現。而在城市視覺文化符號的運用上,「琴澳」的呈現似乎依賴遠處更有視覺辨識度的澳門大三巴牌坊與蓮花,而珠海或橫琴本身則以海浪、海豚或作為國家力量的奇觀展現的跨海大橋來呈現。島內和琴澳之間數量眾多的橋樑,成為「互通互聯」的隱喻。因此從符號的選擇也能大致闡釋特區背後的區域政治意涵:借由澳門的資本主義制度與連接世界的後殖民遺產,輔以由上至下的國家基建力量和政治統籌來發展特區。
富曖昧的「澳門社區」
不遠處,則是由澳門政府旗下都市更新委員會在橫琴島的試驗社區項目「澳門新街坊Novo Bairro de Macau」。深綠色的裝飾藝術風格燈牌、路牌與欄杆、葡式碎石路、藍釉青花瓷磚、中葡雙語的文字,讓人彷彿置身於一塊澳門飛地。除了挪用視覺符號,澳門的社區治理和生活方式也被引至此地,如澳門街坊會、澳門婦聯會、旁邊的澳人子弟學校及澳門標準的衛生所。此外,這裏亦設置24小時自助服務中心,包含辦證機器和其他政務設施。與售樓部工作人員交談了解到,購買此地房產僅限澳門永久居民,但租賃並無限制。他們的銷售話術包含相較於澳門的低廉房價、幾分鐘到口岸的免費接駁、高樓層能直接看到澳門島。在我看來,這個澳門社區的內地移植,蘊含着各種關於邊界的曖昧、消融、妥協、延伸及再造。在促進琴澳一體化的同時,也悖論地依賴着排他的邊界想像去維持。在這裏,內陸的建築工人和清潔工、象徵澳門「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葡殖美學符號、帶有簡體和內地設計特色的路牌和同時播放中央電視台與澳門衛視的餐館有機地共存在一個空間。
總的來說,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仍處於發展初步階段,街上人流較為稀疏,寫字樓也大多仍處於招商空置狀態,宛如一個充滿潛力的樂高藍圖。橫琴合作區讓我們得以思考城市疆域和邊界的意義,得以思考在流動與共融的語境下,何謂一個城市本體——澳門和珠海的城市主體性會因此消失或得以延續,亦為未來的深港邊界北部都會區的規劃與地方營造提供參考價值。
文、圖˙ 鄧浩賢(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博士生)
{ 美術 } 朱勁培
{ 編輯 } 林曉慧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