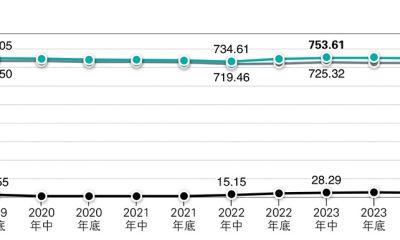觀點
閻小駿、李拉:美國政治的文化轉向及其後果

【明報文章】從今年10月1日開始的美國聯邦政府停擺,截至本文完成之日,已達40天,打破了美國聯邦政府停擺時長的歷史紀錄。政府停擺,是美國兩黨政治的結構錮疾,此次停擺也不例外,直接原因正是由於共和與民主這朝野兩黨僵持不下,美國參議院沒能在政府資金耗盡前通過新的臨時撥款法案而致。雖說如此,超長時間的政府停擺,仍然反映出美國兩黨政爭日趨激烈、國家政治版圖極化(polarization)不斷加劇的現狀。可以說,美國政治當前所呈現的,是前所未有的高對抗、低妥協態勢。
紅藍陣營 對立加劇
過去10年來,美國內部經濟不平等持續加劇,身分認同與文化議題高度極化,加之媒體生態碎片化與社交平台的放大效應,使兩黨選民漸行漸遠,「紅」、「藍」陣營對立加劇,政黨的地域影響力也愈加鞏固——在支持特朗普連任的25個「紅州」,共和黨幾乎完全掌控州長職位、州議會席次;而在反對他的19個「藍州」,民主黨亦展現出類似壟斷局面。曾經,兩黨在對方勢力範圍內仍能保有少數議會席位,但隨着鬥爭升溫,這些力量正逐步消失。
美國的建國者早已意識到,民主政體天生帶有黨爭和分裂傾向。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黨人文集》第十篇中就敏銳指出,美國必須認真處理現代社會利益分化和黨派競爭所帶來的消極負面作用,以最好發揮共和制度的優勢。他寫道:「有產與無產之人,自古即在社會中形成迥異的利益。債權人與債務人,同樣屬於此種區分。地主利益、製造業利益、商業利益、金融資本利益,以及許多較小的利益,必然在文明國家中滋長,並將社會分為抱持不同情感與觀點的各種階層。對這些多元且相互牴觸的利益實行規範,構成了現代立法的主要任務,並使黨派與派系精神滲入政府必要且日常的運作之中。」
在此後兩個多世紀,美國政黨制度的運作大體遵循麥迪遜的觀察,即政黨被視為多元社會利益的代表,而黨爭則是現代社會經濟矛盾的外化。無論是19世紀工業與農業的對立,抑或是20世紀勞資衝突、「99% vs. 1%」等,美國政黨政治多半圍繞財產、稅收、貿易與社會福利等分配議題展開。這類黨爭雖說激烈,惟仍然於共同政治框架與基本國家共識之內運作。
不止「利益之爭」 更是「文化戰爭」
然而時至今日,美國政治與社會的雙重撕裂,似乎呈現新特徵——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分野,不再僅僅反映經濟利益對抗和分配議題上的博弈,而更多地呈現出根植於文化與價值觀差異的更深層分裂。
宗教信仰、族群態度、性別與家庭觀念、移民與多元文化政策,及新媒體平台形成的「迴音室」效應,都重新塑造美國人的政治歸屬感。結果是,原本屬於階級或利益的分歧,轉化成對生活方式、世界觀乃至身分認同的全面對立。麥迪遜所謂由不同利益和階級派生出來的「不同情感和見解」,在今日美國獲得新的生命力。這些情感已不止是附屬於階級階層的利益分化,而是演變成獨立而深刻的政治文化鴻溝。換言之,當下美國的黨派分裂已不僅是「利益之爭」,更是「文化戰爭」——是一場關於價值、身分與國家文化方向的長期對抗。這使當代美國的黨爭更具情感性與排他性,亦更難透過傳統的政治妥協機制來化解。
美國政治的文化轉向,始於20世紀80年代末進步思潮的深刻變化:其關注重點從過去以經濟平等、分配正義與階級階層公平為中心,逐步轉向身分認同、文化價值與文化正義等所謂「進步主義」議題。冷戰結束、全球化程度加深、新自由主義興起,使傳統勞工政治的基礎日漸削弱;產業結構空心化、工會力量衰退,及高等教育擴張,大量受過良好教育、具自由主義理想的新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成為自由主義文化政治的主要支持力量。
全球化與科技革命 帶來新鴻溝
這股「知識精英化」潮流,令美國自由派的政治語言發生了質變。面對全球化與科技革命帶來的新社會鴻溝,民主黨不再以再分配政策或勞工保護為主要訴求,而是轉向強調多元文化、性別平權、少數族裔與環境議題等進步主義價值觀。這種文化面向的政治理念,雖擴大了公民權的定義、促進了社會包容,但也在無形中產生了一種「道德優越感」傾向,使部分未受高等教育、在經濟全球化裏被邊緣化的基層選民群體,感到在新的自由主義政治中被排斥、貶低與背叛。
法國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稱這樣的現象為「婆羅門左派(Brahmin Left)」——由受過高等教育之知識階層主導的改革派政治;與之相對的是「商人右派(Merchant Right)」,代表資本與市場利益。在這種「雙精英結構」下,工人階級與中下層群體(正如美國副總統萬斯的著作《鄉下人的悲歌》所描述)逐漸失去政治代表,進而轉向民族主義、宗教保守主義或民粹主義的懷抱,尋求身分與尊嚴認同。
中下層群體對自由派主導之「文化世界」所產生的疏離和敵意,已日趨尖銳。根據作家Beth Macy在其新書Paper Girl: A Memoir of Home and Family in a Fractured America的採訪,許多居住於美國「紅州」的家庭,父母拒絕供子女上大學,這常常不是出於經濟原因,而是在他們看來,若孩子去了大學,就很可能離開家鄉、進入城市,最終受當地自由主義、進步派價值觀影響,回到家鄉時已變成「另一種人」。這充分反映出美國基層社會對進步文化和文化精英根深柢固的反感。
於是,原本以經濟對立為主軸的美國政治分野,逐步被文化與價值觀的鴻溝取代。當今美國黨派爭鬥,不再僅僅是關於所得稅率或福利政策的辯論,而是涉及「誰的文化能夠代表美國」、「什麼樣的生活方式才是美國」這類更深層的文化認同問題。這是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政治文化轉向的核心,也構成今日美國社會撕裂的根本張力:
一方面,掌握公共話語權的少數知識精英,丟失了民主黨的選民基礎,其結果是民主黨近年在國家選舉政治裏節節敗退。自由派力量轉而以媒體、大學和街頭為陣地,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女性大遊行、維護移民權益及新一輪工會化浪潮中,進一步鞏固了其在關鍵議題上的話語權。然而其文化影響力的擴大,並未能直接轉化為在聯邦層面有效推進政策、拓展治理能力的路徑,更無法掌控國家機關等制度性的權力,因而展現出一種「強文化影響,弱政治權力」格局。
另一方面,捲土重來的共和黨政府,整合了商人右翼和被拋棄的中下層族群力量,利用進步主義價值觀對城郊、鄉村、中西部等地區選民造成的不安,於選舉取得極大優勢,實質上控制了國家司法、立法和行政中樞。惟在社會話語權方面,他們既未能佔據文化高地,更無法媲美自由派的影響力和傳播力。
因此,自由主義文化與保守政治力量形成了一種膠着而糾纏的鬥爭態勢:自由派政策主張愈強調改革與進步,保守派選民就愈視特朗普政府為傳統價值捍衛者;而保守派治理手段愈趨強硬,自由派的街頭運動與社會動員就愈容易得到道義正當性。雙方在相互刺激中,不斷加劇美國撕裂。
政治與文化權力拉鋸
中間協商空間趨收窄
美國國內愈演愈烈的文化戰爭,其結果之一便是政黨政治逐漸傾向保守與現實主義,優先維護秩序、權威與利益;而社會文化領域則日益被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價值觀所支配,倡導多元、平權與道德進步。兩者不僅互不妥協,甚至在根本理念上互相否定。雙方在不斷塑造對方極端形象的過程裏,有效激發了基本盤選民的參與熱情,但也導致中間協商空間日益收窄。這也是兩黨僵局造成聯邦政府停擺背後的政治邏輯。於可見的未來,政治權力與文化權力之間的持續拉鋸,仍將構成美國政治的主旋律。而這種鴻溝還將以何種形式在美國政治裏具體表現出來,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閻小駿是港大中國制度研究中心總監,李拉是港大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研究)
■稿例
1.論壇版為公開園地,歡迎投稿。論壇版文章以2300字為限。讀者來函請電郵至[email protected],傳真﹕2898 3783。
2.本報編輯基於篇幅所限,保留文章刪節權,惟以力求保持文章主要論點及立場為原則﹔如不欲文章被刪節,請註明。
3.來稿請附上作者真實姓名及聯絡方法(可用筆名發表),請勿一稿兩投﹔若不適用,恕不另行通知,除附回郵資者外,本報將不予退稿。
4. 投稿者注意:當文章被刊登後,本報即擁有該文章的本地獨家中文出版權,本報權利並包括轉載被刊登的投稿文章於本地及海外媒體(包括電子媒體,如互聯網站等)。此外,本報有權將該文章的複印許可使用權授予有關的複印授權公司及組織。本報上述權利絕不影響投稿者的版權及其權利利益。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閻小駿、李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