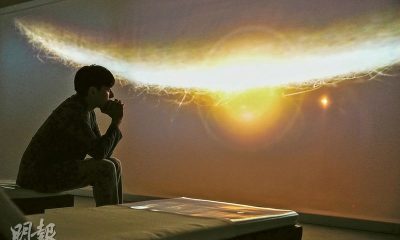副刊
拍賣行舵手遊戲人間 程壽康玩出收藏大智慧

【明報專訊】在佳士得亞洲區主席程壽康的IG,上載有不少其個人搞鬼照片。有身穿帶點David Hockney感覺的翠綠毛衣,手捧着名瓷器藏家區百齡珍藏的「豇豆紅釉萊菔尊」;又有他模仿Labubu的神態,跟這隻潮物的合照。自言IG上的相均是他自編自導,遊戲人間的他更笑說:「佳士得請我復出時,我說我的形象是喜歡玩,我會繼續這樣,如果你覺得會影響公司形象,不要叫我來。」
曾任孖士打律師行合伙人、上市公司法律顧問,前半生周旋商業法律條文之間,人到中年轉換跑道加入蘇富比,退休後當上佳士得亞洲區主席,全球兩家最大的拍賣行都服務過,明年踏入拍賣行業20年的程壽康,還有什麼想玩,什麼想藏?
一對「核桃」開啟收藏路
很多人知道程壽康(Kevin)愛玉,但他自言收藏跟從事拍賣並沒有絲毫關係。他為專訪帶來的珍藏並沒有古玉,反而有4顆文玩核桃,其中兩顆正是引領他展開收藏之路。1987年,當時他被孖士打律師行派駐北京開荒,駐京兩年的Kevin走遍京城巷子的跳蚤市場,這兩棵清朝核桃就是當年撿地攤時買來的。「有段時間核桃炒得很貴,一對賣到幾十萬甚至100萬元。但我買的時候很便宜,這對(核桃)玩到『瓷化』了,顏色都滑了。核桃要一對、對稱,有些叫官帽,有些叫獅子頭,(不同形狀)不同名……你當它們是太陽和月亮。『掌上旋日月,時光欲倒流,周身氣血湧,何年是白頭。』我現時睡醒覺血氣不好,手指有點硬,回到辦公室就這樣弄一弄(轉核桃),很有益。」今年69歲的程壽康說。
1987年,他第一次上京,街上民眾都是騎單車,他入鄉隨俗,花了270元外匯券買了一架鳳凰牌單車,踩着車四處看故宮、古建築、藝術館,想起小時候讀的《風雪中的北平》不就是眼前的景况嗎?「那兩年北京生活是我怎樣都不願換走的,是人生轉捩點,(讓我)愛上了中國文化。」在跳蚤市場,他發現什麼東西也有人玩,「火柴盒、小人書(漫畫),有錢的有錢玩,沒錢的也有沒錢的玩法,花鳥蟲魚,這些文化東西,我很陶醉其中」。
中學的他念喇沙書院,雖然念理科,但非常文青,經常看徐志摩的作品,愛寫詩;在英國讀書時又養成寫信習慣。講究的他說:「要用墨水筆,手寫字要漂亮,信封要好,寫得得體。」他又說:「那時沒有電郵,每天等郵車派信……女生還會在信封貼口處寫上SWALK,就是sealed with a loving kiss的意思!」說畢他在透明文件套中抽出一個信封,上面抄寫了劉大白的詩作《郵吻》;隨手一翻,又抽出多張他近年的書法作品,「我跟馮康侯(著名書法篆刻家)的新抱(兼徒弟區二連)學了6、7年書法,每周六朝早7、8點一班人學,別人臨摹碑帖、心經,但我不夠專注又喜歡聊天,老師讓我寫自己風格,我就發神經自己亂做」。古靈精怪的他,就在上課時盡情盡興,把朋友送他的高郵鹹鴨蛋紙箱上的產品資訊、石塘嘴「紅牌阿姑」素梅的詩作,甚至林覺民跟妻子陳意映訣別時寫的《與妻書》……以小楷寫下,總之想到什麼寫什麼,貪玩的他更把程壽康版的《與妻書》,加上火燒信紙效果,這還未夠激,最後送上「血掌印」,扮作遺書,絕對是無聊事認真做的先驅。
兼顧內外 專家與賣家同樣看重
看到這裏,你大概知道他是個怎麼樣的人?雖然看似天馬行空、遊戲人間,但其實他的人生,正路到不得了。1970年代他到英國念書,母親希望他念醫行醫,他卻執意念法律,念碩士時研究當時兩大共產黨——中國和當時的蘇聯法律體系,其後在英國、香港執業,亦曾加入孖士打律師行,當時主攻內地商貿法律事務。及後被潘廸生羅致旗下發展內地業務。在廸生集團工作的第5年,蘇富比首次向他招手,卻被當時老闆潘廸生擋下。其後時任佳士得亞洲區主席林華田想找他接任,卻被早年向他招手的蘇富比美國CEO得悉,最後他加入蘇富比成為亞洲區CEO,二人「再續前緣」,直至65歲退休。之後不同畫廊及其他機構力邀他復出,最終加入佳士得。
一般人大抵認為要從事拍賣行業,「藝術底」必須極強,Kevin卻認為要營運這門生意,懂得待人接物的高EQ才是致勝關鍵,「這一方面我是叻的,我的凝聚力在行內是有點名氣的」。他說不少人認為拍賣講究的是物件,但其實人與物同樣重要。「第一是同事,專家是我們最大的資產,這不是在牛津劍橋就能找得到,讀書學的是art history,你做博士很厲害?我給你一件東西,你要懂得辨識。(拍賣行)專家是從小學師,做圖錄員寫拍品資料,師父會教他們怎樣看。街上有多少人懂得看瓷器、分真假?他們(專家)有藝術家的個性,知自己斤両,所以對內要懂得跟這些人共處,令團隊有凝聚力。對外,客人都是有錢人,就算上茶樓,茶客也永遠是對的,何况他們花這麼多錢買東西,如果不開心,可以有很大脾氣。如果他們不滿意,你怎麼在客服方面處理?怎麼哄到他們給你賣、買你的東西?」
藝術市場的「非理性繁榮」
在疫情下,2021年是佳士得香港拍賣成績的破紀錄年份,惟近年整體拍賣市場呈下行趨勢。「當市場下行,我們選東西就要貴精不貴多,東西愈漂亮愈稀有,又流傳有緒,人們覺得開價合理,拍賣成績一樣會衝上去。」他舉例,2023年天民樓珍藏15件元青花和明清官窰瓷器就合拍了2億多元,去年高古玉拍賣專場落槌總額更為「低估價」的近6倍。「我們收回來的東西,可能5年後會很厲害,現在沒人會知道,有點像股票。但股票是supply and demand,藝術不是,不需那麼多人追捧。藝術市場有irrational exuberance(非理性繁榮)的說法,就算全世界不喜歡的東西也不要緊,拍賣時有兩個人喜歡就爭到癲。之前有件畢加索作品賣了2億元,1億以後的叫價只是由兩個競投者每口價1000萬元加起來的,就是因為有人跟你爭,你又不肯輸;如果其中一個停了叫價,那幅畫1億元就賣出了。」加上競投者的口味變化,即使是專家也猜不到。「如果我入行時(向人)借錢買了中國當代畫、買趙無極,我都發達啦。有誰想到接下來什麼會飛升?以前不是很流行唐三彩馬、乾隆五顏六色的官窰嗎?現在人們玩宋朝瓷器,喜歡清淡,覺得較有文化感。」
收藏界裏有一句:There is always another,程壽康的演繹大概是,收藏家對一件自己很喜歡的物品,都會「恨到口水流」,千方百計以高價奪得,給自己的借口就是「我買了之後就會滿足」。事實卻是,到手一星期後就已經忘了舊的好。「人不是貪新忘舊,而是貪得無厭。」作為拍賣行的亞洲區主理人,他既拍也藏,多年來藏有不少心頭好,不過他知道孩子對他的玉石收藏沒有興趣,「如果是幾隻Patek Philippe、Rolex腕表可能還好點。人到了知命之年,就開始question擁有的意義,我自己也是這樣。我還買這麼多來做什麼」?他鼓勵其他藏家趁有精力時,就好好地有系統地處理藏品。
至於現時拍賣場上的趨勢,他說:「中國當代藝術有段時間很強,但現在回落。大家都喜歡奈良美智、草間彌生,印象派的莫內、近代的畢加索。現在社會步伐很快,有錢的人都是40多歲,做finance、晶片、tech的,你看做crypto(加密貨幣)賺到多少億……在你讀歷史時,他已多賺了幾千萬元了,哪有心機慢慢了解。一隻幾百萬元『豉油碟』放在家裏,誰知道這是什麼呢?你放一幅名畫(出來),大家一進來就覺得威風了。」他認為現時不單中國文物,連維多利亞時期畫作、外國古董家具的銷情均不佳,不過他始終相信「文化自信」的重要:「培養人們欣賞、傳承自己的藝術,懂得保護,懂得買,懂得投資;現在有一班畫國畫的新一代很好,中國水墨畫、新派水墨畫是有發展的。」
文:張曉冬
採訪:張曉冬、陳詠詩
設計:賴雋旼
編輯:鍾卓言
[開眼 收藏]
日報新聞-相關報道:
「飽暖思藝術」 (2025-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