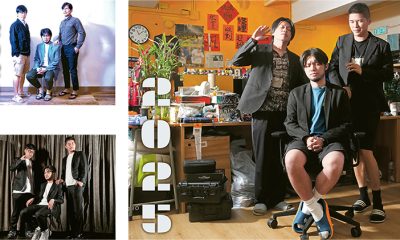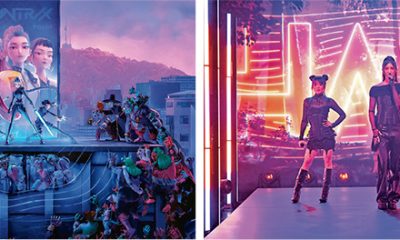副刊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恍如我們都是歷史的天使——和人類學學者項飆談生活質感的重建

【明報專訊】在今時今日的中國知識青年當中,「項飆」是個關注度十分高的名字。畢業於北京大學與牛津大學的人類學者項飆,近年在內地頻頻曝光,從拋出「把自己作為方法」、「附近的消失」等概念到更早前介入內捲、躺平等的討論,都看到他與時下年輕人的緊密互動與共振。他深度參與的書籍《你好,陌生人》年中在內地出版了,我讀完後覺得很有啟發,也很榮幸邀請到他進行了線上的訪談,進一步了解他對年輕人的觀察,以及其自我定位。
s:sunfai 項:項飆
s:項飆老師,可以先請你介紹《你好,陌生人》出版的緣由麼?
項:2022年,《三聯生活周刊》想就「附近」這議題做個專題,我有幸參與其中。稿件回來後我們發現內容多為些周邊環境的直接描寫,沒有什麼思想性,不大好看。後來我覺得要較深入的談「附近」,可能需要個切入點,建議可試着從觀察身邊的陌生人開始。
我是從「附近的消失」這思考出發,關心以上的探討的。在中國日益原子化、沒有自發的社會組織形成的情况下,人們、特別是青年們都感到沒法控制自己的生活,被某種巨大的事情捲着走。青年人感受不到生活的質地(texture),情緒很容易被社交媒體、流量帶着走,缺乏穩定的、安生的感覺。我們希望大家透過重新學會看見別人,重新建立起生活的質地感,讓生活摸上去不是一味平滑、像空氣一樣。
另外,在疫情中間人們生活都頗為壓抑、失去控制,而生活中突然間出現了像防疫人員、社區居委那樣的「陌生人」。像2022年中,有名上海居民家附近的電話亭裏住了一個陌生人,大概是因為疫情封控無法回家吧,居民拍下那情景並把照片放了上網,引起了很多關注,也啟發了我。透過認識陌生人、猜想陌生人,也許能讓我們對附近及自己的生活有更直接的感觸。
因此我和三聯的同事便邀請了5位實踐者來對談:畫家劉小東、人類學博士與媒體人何襪皮、紀錄片導演李一凡、社區花園推動者劉悅來教授、南京市紅山森林動物園園長沈志軍。我們特意找實踐者而不是學者,因為學者說話容易概念化,但跟實踐者談就會更具體,談很多細節。我不是認為年輕人都需要達到對談嘉賓們的能力,但希望青年朋友們能對此有所認識。
我們也想透過對談來呈現,討論是可以深化想法的。討論對建設公共空間十分重要,但國內目前這方面做得不夠好。透過對談及書的出版,我們想展示怎麼從了解、看見陌生人來重構對生活的感知,以及討論的藝術本身。
s:我知道你對社交媒體上情緒化、立場為先的表達有所反思,所以上邊提到的對談安排,以及推動青年的討論與參與,也有區別於社交媒體上的那種方式的想法在嗎?
項:對的,可以說我們是刻意為之的。
提出「附近」的概念,其實就是希望大家能看到事情本身,在具體的語境(context)中講清楚其內容。這和在社交媒體上牽引着年輕人情緒的「遠方的事情」很不一樣。「遠方的事情」很多時和事情本身沒什麼關係,卻有着強烈的情緒與意識形態色彩,表達很立場化。而相反的是,發現附近的樂趣正正是來自於對細節的觀察,以及細節背後種種讓人驚訝的東西。
聚焦平常、具體的事情
另外,我們這次對話的特點與風格,也與社交媒體上的、情緒化的形式有所區別。我們不是在談很宏大的抽象論述,而是去談些很平常的、非常具體的事情。比如劉小東會跟我們分享他如何選(被畫的)人:看人的背面,看他的肌肉而非眼神,因眼神會騙人,但肌肉、姿勢卻不會等。這種細節的分享就很感人。
s:可以邀請你再談一談,「陌生人」這概念能幫助我們觀察到中國社會的哪些現象嗎?
項:首先想說明,「陌生人」不是以研究課題被提出的,它更多是一個切入點讓我們重建附近。
在微觀的層面,我們觀察到的是「陌生化」的普遍化。本來在城市或現代生活裏,存在陌生人並不奇怪。在中國的情况是,由於監控技術的提升等,大家其實並不怕陌生人,因陌生人帶來威脅的機會已變得很低。大家怕的卻是從陌生人變為熟人,擔心因此會帶來傷害。大家十分害別向別人打開自己,也害怕別人向自己打開,並極力維持一種陌生的關係。因為這樣,大家都擁有非常強的孤獨感。
舉例,在調查裏我聽說過,在4人合租的青年公寓裏,大家可以在共居半年以上而互不認識,並會用盡方法來避免見面。現在年輕人基本靠外賣,故不會因要煮食而在廚房見到,廚房都極其乾淨。如在離開自己房間前聽到別人活動的聲音,會等別人離開後才出去,避免碰到。
長久下去,人們對自己是誰愈來愈沒有把握。自己究竟要什麼,想的東西是否真實等都無法在與別人互動裏得到確認。有些人還出現「愛無能」的情况,即因不信任別人而不敢去愛,因不知道自己是誰而不能接受愛等。這種對自我的懷疑與不把握,讓自己也變成了自己的陌生人。
宏觀地看,這當然和中國的政治經濟狀况有關,我在書的序言中也分享了些想法。比如所謂的「透明不透氣」,即所有事情和規則都很透明(特別是在科技下),但人與人之間卻很難交流。自我強制性地與別人割裂,有很強的邊界感等,都與目前的城市生活構造很有關係。
s:那這些問題是中國特有的嗎?和別的地方相比有什麼,中國的情况有什麼特點?
項:這不是中國特有的,比如韓國也有很高的自殺率,日本社會的孤獨情况也廣受討論……西歐也有類似的問題。
但中國獨特的地方在於,這些情况更為普遍,表現的形式也比較突出。比如目前青少年的心靈健康問題就上升得很迅速,輟學、住院甚至自殺都在增加中。又或過去中國社會本來很講究關係,邊界感非常弱,但一下子變得邊界感十分清晰。與此同時,社會尚未有相關的語言及心理機制去應對。
資訊科技的發展與變化,在西方和中國同樣帶來了影響,也是導致以上問題的原因之一。而在中國,教育以及職場的內捲,白熱化的競爭,目標的單一化讓問題更加突出。另外,獨生子女也是中國特有的情况。獨生子女不止意味着沒有兄弟姐妹,更重要的是他們都在大人們的凝視下成長,一直面對着、迎合着一個巨大的權威。成年人當然也會給予關愛、給予資源,但長期面對一個巨大的體系也會造成孤獨感。
s:我也注意到,中國社會的功利主義、目標單一化是你特別想回應的話題。所以可否說你正在提出新的價值觀?
項:我們更多是希望提供方法。當然打破社會只有唯一的價值觀、只有一種玩法是首要的。
接下去其實需要每個人在生活經驗裏、在和別人的關係裏去體察,自己想要怎樣的價值理念、想要過怎樣的生活。這也是為什麼提出「重建附近」是重要的,因它是一種探索哪些價值適合自己的具體方法。
s:那幾年下來,透過「重建附近」、「看見陌生人」的討論,你看見了什麼變化麼?
項:我觀察到年輕人興起了反思的意識,也就是說他們意識到自己的生活出了問題,不然就不必來讀我們的書,或參與相關的討論了。他們或許尚未能指出問題究竟出在哪裏,或者不知道如何解決,但都願意思考。這對我來說是極大的鼓舞,也是對社會學者提出了要求。我們不一定能給予答案,也不需要給答案,但起碼應給予回應,提出思考的線索、行動的抓手等。
小實驗正在發生
反思意識更強,更多人在思考相關的問題,也帶來了意識上的鬆動。過去他們可能也對生活只有單一的目標感到不高興,比如教育就是為了考某些大學呀,工作便是唯一的意義來源呀,又或家裏催婚催買房呀,但都沒有什麼辦法。現在他們可能會覺得這不是唯一的,開始探索各式各樣的生活方式。
具體來說有很多小的實驗在發生,比如組織讀書小組啦,建設社區花園啦。也有不少人透過拍攝記錄自己生活裏的附近、陌生人及家庭生活,也有人在嘗試非虛構寫作。
但這會否形成系統性的變化,並不好說,畢竟探索的時間太短,問題也比較複雜。
s:回過頭看,這幾年的討論有什麼尚待深化的地方嗎?
項:中國的青年對階級性、不平等的問題都很敏銳,但對不平等的強調也會帶來無力感、怨憤,甚至讓他們提出來的解釋變得過於粗糙,比如「一切都是黑暗的」、「社會都要把我毒打」等。這種批判未必能能給予我們力量,甚至有點self-destructive。
當我們說大的環境和結構改變不了,可先在小的、可控的範圍內(像附近)行動,那接着的問題便是如何在「附近」中看到與社會結構的關係,知道自己在大的格局裏,並有意識地自處和行動,又能避免助長我們所關心的不平等。這部分我們過去涉及得不多,也因此有些朋友會提出批評。
談大的結構本身是容易的,關鍵是如何在具體的生活裏看到結構,並知道如何形成有效的應對,這在理論上、實踐上都需要進一步的探索和突破。
s:你提到青年人的反饋給予你很大鼓舞,也對社會學者提出了新的要求。這幾年你十分活躍,也提出了諸如「懸浮」、「把自己作為方法」、「附近的消失」、「看見附近/陌生人」等不同引起關注的想法。以上的實踐,與你對學者的自我定位有沒有關係?這種定位在學界普遍麼?
項:我的工作方式一直是互動式的,希望參與到公共討論中。在過程中感觸最深的事情,往往會成為我下一個研究的關注。比如當時提出「附近的消失」,是希望去解釋為什麼在懸浮、內捲的情况下沒有出現更明顯的抵抗;而上邊也談到,因為想重建附近,我們提出了可從看見陌生人入手。以上都和我對common concerns(共同的關切)的關心有關。包括現在對「無力感」、「勇氣」等的關心與書寫,很多內容都來自或得益於青年人給我的反饋。
回應大眾、參與到公共議題,確實是我作為學者的一個定位,或至少是我的願望與方向,不一定能做到。過去哲學界和社會學界參與到公共討論的學者比較多,像沙特、漢娜‧鄂蘭、馬庫色甚至法蘭克福學派等,也包括當代的齊澤克、韓炳哲等,文藝界和性別研究的學者也與社會較多互動,但人類學者則少一點。
我很感激與社會的互動、青年人給予我的反饋,以及不同人給我的批評,這些都會為我帶來激發,是讓我繼續成長的營養。
s:最後,我想問你一個和香港相關的問題。現在,香港與內地融合既是主旋律,也是大趨勢,但官方的敘事並不吸引,也未必能幫助我們認識中國社會在發生什麼。面對這情景,我們可以如何自處?你對讀者有什麼建議麼?
項:這種感受,與內地年輕人的感觸好像也有類似的地方,大家都面臨着一種「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必然趨勢」的敘事。歷史的車輪就是往這方向駛了,同不同意也必須上車。
我沒有在香港生活過,也對現在的香港社會沒有具體感知。但當你這樣提問時,班雅明「歷史的天使」(Angel of History)的意象在我腦海裏浮現。歷史的天使面朝過去的廢墟——我們可以把廢墟理解為眼下的附近、生活。歷史的大風不斷把天使往前吹,讓她無法抱住那些廢墟。我們每個人都像歷史的天使那樣被風吹着,無法阻擋,也無法退出,只能繼續前行。歷史大輪也像是在告訴我們,自己的生活、附近、記憶都會成為過去,成為廢墟的一部分。
在風中抱緊廢墟
但在停不住大風的當下、在這樣的歷史時刻,我總覺得盡量抱住被吹散的廢墟,哪怕是其中一點點灰燼都非常重要。多一點理解附近、跟大地貼近一些、更能感受到自己的重量,這樣我們的生活意義感會豐滿一些,也能給其他人或後代留下更多的歷史記憶與述說。
我自己的研究受着存在主義、現象學等的影響。作為人類學者,我沒有能力去改變歷史的風向,而是希望讓風裏的人有更多的力量、對自己有更多的認知。當有更多人有力量感時,或許風會慢下來、會轉向,誰能說得準呢?就算歷史的大風最後沒有任何改變,這過程本身對我來說就是有價值的。
後記:重建的切入點
在訪問中項老師也談到,有人會批評他提「重建附近」有什麼意義呢?能改變什麼嗎?他說自己也不知道能改變什麼,特別是如果我們不關心別人心裏想什麼、有什麼感受、生命是怎樣走過來的,那最後當然可以把一切歸因到權力決定一切的邏輯。但或許恰恰是他那種「認命但不認輸」的取態,讓那麼多面對人生困惑的年輕人能從他身上找到共鳴和啟發,並在不無壓抑的中國社會中掀起不大不小的異樣。
在〈人重新站在大地上:「附近」的保守和熱情〉一文中項飆寫到,在面對商業單位、行政控制單位和技術控制單位把生活高度整合的超現代性時,「附近」的提出是要「保護人的主體性,或者更精確地說,保護人的主體性的完整、多面和具體的特性」,並讓我們「注意辦公室、工地、公共車廂這樣的附近,把原來覺得轉瞬即逝、毫無意義卻每天長期置身的場所變成生活裏有意識的一部分」。附近也好,陌生人也好,都是讓我們建構生活的工具或切入點。但願我們都能建立起對生活的質感,在具體的場景中找到與結構對話和博弈的位置,哪怕眼下一切到最後都可能煙消雲散。
■答•項飆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
■問•sunfai
社區工作者,喜歡閱讀
文˙sunfai
編輯˙王翠麗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