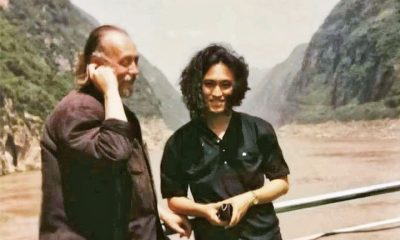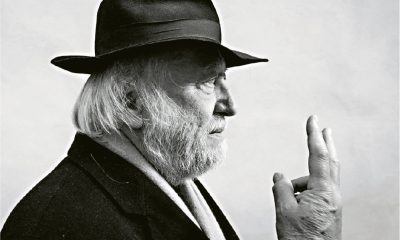副刊
A to Z藝術字典:R-Relational Aesthetics 關係美學

【明報專訊】之前我們已經談過很多,當代藝術早已不再只是用來觀賞或收藏的物件,而是有更多可能。它甚至可以成為一種人際互動的場域。藝術不止拿來看,還能讓人參與、互動,甚至改變我們與他人的關係。今期就讓我們談談「關係美學」(Relational Aesthetics)。
以人際互動為核心
關係美學是法國重量級藝評人兼策展人尼可拉‧布里歐(Nicolas Bourriaud,1965-)在1990年代提出的重要概念。他於1996年在波爾多現代藝術館(CAPC)策劃展覽Traffic時首次使用此詞,並具體實踐這種以人際互動為核心的藝術形式。1998年他出版了著作《關係美學》(法文原名Esthétique relationnelle,英文版譯名Relational Aesthetics),有系統地進一步闡述這個概念。
關係美學強調藝術不止是被觀看的對象,而是一種讓人參與、交流、共同經驗的社會行動。也就是說,藝術的重點不在於創作出一件物品讓人欣賞,而是在於創造一個讓人們可以互動、溝通,甚至建立關係的情境。例如,觀眾可能被邀請參與一場對話、一起用餐、分享記憶,或在特定空間中與他人一起完成某種行為。在這樣的藝術實踐中,人的參與本身就是作品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說,作品是在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中「產生」的。
傳統社群解體 人與人需重新連結
關係美學的興起與20世紀末全球社會結構的快速變動息息相關。戰後的都市化與全球化導致大量人口流動與資訊交流,深刻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模式。傳統穩定的社群逐漸解體,人們在多元且流動的城市中,開始尋找新的連結與歸屬感。這樣的社會轉變引發藝術家的關注,許多人開始聚焦人際關係的變化,並嘗試透過藝術行動來回應、介入,甚至重塑社會連結。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藝術被視為促進人與人之間互動的「社會空隙」(Social Interstice)。所謂「社會空隙」是指那些不受日常規範限制的空間,使人們能在主流體制以外,進行真正的社會互動與連結。這些空隙並非固定的場所,而是透過人際關係的建立而成。藝術在其中扮演重要橋樑,開啟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進而創造出一種不同於商品交換或權力結構的社會場域。
記得2020年,大館曾舉辦比利時概念藝術家法蘭西斯‧艾利斯(Francis Alÿs,1959-)的展覽《水限_陸界:邊境與遊戲》。他的創作經常結合公眾參與,那次展覽也不例外,其中一件作品就邀請了一群參與者走進大館廣場,隨機接近坐着的觀眾,低聲講述自己藏在心底的故事。我還記得當時有一位女生走到我面前,分享了她與母親的複雜關係。她說,在母親眼中自己永遠不夠好,無論多努力,都得不到真正的肯定。那種從未被認同的感覺,即使在長大成人後,仍像一根藏在心底的刺。聽着聽着,我不禁雙眼通紅。因艾利斯的作品,我們與陌生人拉近,分享了一段短暫的私密時光。聽者因別人的故事動容,而說故事的人或許在重述的過程中,亦得到某種釋懷。
社會轉型影響藝術實踐
當代社會正經歷從「商品經濟」(commodity economy)邁向「服務經濟」(service economy)的結構轉型,這一變化也深刻影響了藝術的生產與接受方式。傳統上,藝術被視為具物質性的「作品」,可被收藏、交易與擁有;但在服務導向的社會中,藝術的價值不再僅僅依賴其作為「物」的存在,而是轉向以過程、經驗與互動為核心。藝術家不再只是創造靜態作品的「製造者」,更像是關係的「促成者」、情境的「設計者」。藝術的實踐重點也從創作物本身,轉向人與人之間如何透過藝術產生連結,並在參與的過程中賦予意義。
以泰國藝術家里克利‧提拉瓦尼(Rirkrit Tiravanija,1961-)於1990年創作的作品Pad Thai為例,他在紐約Paula Allen畫廊展覽期間,將空間轉變成臨時廚房,親自現場烹煮泰式炒河粉(Pad Thai),並免費分送給觀眾品嘗。觀眾不再只是旁觀者,而是成為參與者,一同用餐、交流,透過共享這頓飯,與藝術家及其他觀眾共同創造了一段互動經驗。此作品同時探討了文化身分與飲食文化的議題。作為泰國極具代表性的國民料理,Pad Thai不僅被帶入當代藝術的語境,也成為藝術家個人文化背景的具體展現與對話載體。
除了里克利‧提拉瓦尼查的作品外,香港藝術家黃志恆與梁志和也於1999年至2003年間共同創作了《城市曲奇》(City Cookie)系列。這組作品以日常生活的視角,重新探索人們對城市空間的感知。在《城市曲奇》中,兩位藝術家從不同城市的照片中擷取建築物間天空的輪廓,將其轉化為餅乾模具,再以這些模具製作成餅乾,分發給觀眾品嘗;有時甚至邀請公眾一同參與製作過程。這些餅乾不僅是食物的分享,更是對城市經驗的象徵性轉化,讓人在品嘗曲奇的同時,也能重新思考自身與城市空間的關係。
打破單向觀看模式
「關係美學」不僅改變了藝術的創作方式,也徹底革新了我們欣賞藝術的體驗。它打破了傳統美術館中「作品─觀眾」的單向觀看模式,使藝術變得更加民主化,拉近了藝術與大眾之間的距離。因而,造訪美術館不再只是被動的觀賞行為,而成為一場積極參與、互動交流的公共體驗。
美國藝術家米高‧拉柯維茲(Michael Rakowitz,1973年-)自2003年起持續創作的《敵人廚房》(Enemy Kitchen)是一項融合食物、記憶與政治的參與式藝術計劃。拉柯維茲出身伊拉克猶太人家庭,深刻理解食物在文化傳承中的重要性。他與母親及祖母一同整理伊拉克傳統食譜,並邀請伊拉克裔移民與美國退伍軍人共同烹飪,透過「共煮共食」的方式,向公眾分享伊拉克料理。在部分城市,這項計劃更以街頭餐車的形式呈現,觀眾不僅品嘗美食,還能與廚師交流,從中認識另一種文化及其背後的歷史創傷。拉柯維茲透過料理撫慰鄉愁,更借此探討戰爭、遷徙與文化記憶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延續與轉化。以食物這一最基本且富含情感連結的媒介,他創造出跨文化對話的場域,讓過去的敵對雙方能夠共聚一堂,彼此傾聽與理解。
關係美學的爭議
然而,關係美學的實踐並非沒有爭議。英國藝術評論家克萊兒‧畢夏普(Claire Bishop)曾指出,雖然這類作品強調觀眾參與和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但這些互動往往是由藝術家與策展人精心設計,觀眾其實只是被動地執行一套預設好的參與模式。以古巴藝術家塔尼亞‧布魯蓋拉(Tania Bruguera,1968-)於2008年創作的《塔特林的耳語第5號》(Tatlin’s Whisper #5)為例,她安排兩名騎警進入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的大廳,模擬警方在控制群眾時的行動,對觀眾下達如移動、停止甚至驅離等命令。觀眾表面上看似參與了藝術行為,實際上卻是在一個無法選擇、充滿壓迫感的權力場域中互動。這件作品正好揭示了所謂的「參與」不必然等同於「民主」,反而可能加深了藝術中隱而未見的權力不均。
儘管關係美學強調互動、共享與非物質性,但這些作品多半還是在特定的藝術體制之下運作,包括展覽空間、美術館機構、藝術家身分、資助系統及藝評市場等。某些案例甚至讓人感覺,所謂的「參與」不過是一場由少數藝術圈內人士發起的「小眾遊戲」,一群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白盒子空間裏進行某種行動。這樣的藝術實踐表面上反抗商品化,實際上卻仍在資本主義體制與藝術權力核心內。換言之,即使不再創作具體可販售的藝術品,關係導向的作品本身仍可能成為一種可被消費的「經驗商品」,使「參與」淪為另一種資本流動與象徵權力的形式。
無論對關係美學持支持或批評態度,我們都不得不承認,其強調的「共同體」、「交流」與「共享經驗」深刻影響了當代藝術的發展。它改變了我們對藝術的想像,也為公共藝術、參與式藝術(Participatory art)與社會性藝術(Socially engaged art)開闢了新的可能,使藝術成為回應社會議題、介入現實生活、激發公共意識的重要形式。在當代藝術日益重視參與性與社會性的趨勢下,關係美學無疑提供了一個充滿啟發的理論框架。
文˙ 葉曉燕
{ 圖 } 網上圖片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王翠麗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