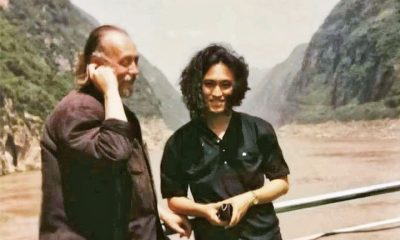副刊
同場加映:預習末日?不,末日早已降臨——從貝拉塔爾看克拉斯諾霍爾卡伊

【明報專訊】一片漆黑,好不容易看見兩父女對坐桌子兩旁,兩人面前放著食物。父親對一臉愁容的女兒說:「吃吧。」見對方沒反應,補上一句:「我們總得吃點。」他自己咬了一口,但隨著女兒堅持沒吃,他停下來,彷彿終於放棄了。畫面重歸黑暗……
這是被視為當代最後一位電影大師,匈牙利導演貝拉塔爾(Bela Tarr)最後一部長片《都靈老馬》(The Turin Horse, 2011)最後一個鏡頭,而這部傑作的編劇就是新鮮出爐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諾霍爾卡伊(László Krasznahorkai)。
用上這麼多「最後」,因為那大抵是形容貝拉塔爾和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最恰當的詞語。兩人堪稱「最佳拍檔」,貝拉塔爾後期五部長片作品編劇都掛上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名字,其中《撒旦探戈》(Satantango,1994)和《殘缺的和聲》(Werckmeister Harmonies,2000)更直接改編自後者頭兩本小說《撒旦探戈》(1985)和《反抗的憂鬱》(The Melancholy of Resistance,1989)。這些作品(無論小說或電影)幾乎都以「終結」(End)為主題,充斥各種反烏托邦和末日意象,將精神自傳統「枷鎖」解放後無所適從,過度自由的心靈陷入憂鬱的後現代狀况體現得淋漓盡致。
小說長句與電影長鏡彼此對照
作為電影愛好者,我的確是透過貝拉塔爾認識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相信沒有誰看完七個小時的電影《撒旦探戈》之後,不對原著感到一定程度的興趣。小說《撒旦探戈》正值後現代書寫逐步成為文化熱潮之際面世,眾聲喧嘩、多角度非線性敘事、後設敘事……種種創新的寫作和閱讀策略都可在裏面尋覓。全書十二章,以前六後六的探戈舞步為結構,一章一段,綿密的長句令我們似須一氣呵成,又不得不中途按自己的節奏暫緩閱讀。「故事」的場景——與世隔絕的匈牙利鄉間小鎮,在在令我想起「小國寡民」的老子理想,但當然那是倒轉了的,就像唐君毅先生在《人生的體驗續篇》表述的種種顛倒相。
看過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文字,會令我們更清楚貝拉塔爾在影像上的選擇。前者的長句與後者的長鏡彼此對照,互相輝映。《撒旦探戈》全片長440分鐘,一共只有約150個鏡頭;《殘缺的和聲》全長145分鐘,更少至39個鏡頭。兩片的鏡頭,不少長達10分鐘,換言之,導演乃用盡一卷35mm菲林的長度,不停機地拍攝進行中的人事。長鏡頭素來要求精準的場面調度和別出心裁的影機運動;在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文本的協助下,貝拉塔爾在這方面表現深刻透徹,得心應手。
就以《殘缺的和聲》的高潮戲為例,村民在沒有露面的王子「煽動」下,發起了暴動,他們攻入醫院,逐間病房破壞,毆打病人。克拉斯諾霍爾卡伊一大堆沒分段的文字,其中一截如此寫道:
「他們有的時候散開行動,三個一群,兩個一夥,有的時候又聚在一起,如洪水一般滾滾向前,但一旦遇到一個完全手無寸鐵的受害者,他們就會立刻失去方寸,楞在那裡不知所措,不明白發生了甚麼。[……]他們被迫認識到,並且不得不承認,這種地獄般的邪惡命已無以為繼,他們殺氣騰騰的凶煞氣勢突然喪失。[……]他們並沒有能完成毀滅一切的任務,現在,他們突然感覺到,在自己身上突然增添了難以承受的心理重荷。經過一陣猶豫不安的躊躇,他們終於從醫院的大門口離開。」(浙江文藝出版社中譯本,頁117,余澤民譯)
貝拉塔爾僅用兩個長鏡頭拍攝這場暴動。第一個以升降鏡頭俯拍(高抄)默默前進的群眾,影機時有對個別村民的上半身特寫,但由於沒有剪斷,集體感便很強,觀眾宛如置身他們之中,見證他們穩定而一致的步伐,都朝一個方向,好像很堅決,很明確地前行。這個鏡頭維持了好幾分鐘,全無配樂,只有腳步聲。下一個鏡頭則先影着醫院的走廊,隨着村民一個個湧入,鏡頭接近冷酷地追蹤捕捉他們沒由來的破壞、把病人拖下牀毒打;有病人朝鏡頭走來,被截住,撲倒在地。依舊沒有配樂,沒有聲張,甚至原著寫有的護士尖叫聲也被導演略去了,無意義的暴力被放大到一個地步,當大家來到一幅布幔前,有人大力把它拉開,裏面站着一個骨瘦如柴,全身赤裸的年老病人,雙目無神地望向人群,彷彿在等待被施虐。所有動作停下來了,然後大家轉身,默默離開,戾氣消失殆盡。原文那一句「直到遇到一個完全手無寸鐵的受害者」,在電影裏以幾何級數的力度呈現。如此對讀之後,稱貝拉塔爾為電影的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是文學的貝拉塔爾,當無異議。
《反抗的憂鬱》寫於「蘇東波」匈牙利變天前夕,脫離蘇聯控制後國民何去何從,顯然是小說潛在的政治主題。儘管如此,克拉斯諾霍爾卡伊選擇了較抽離的手法,為哲化敘事和形而上詮釋提供了空間。整個「故事」並不現實卻又無比真實——生活愈來愈艱難的小鎮,突然收到一個神秘馬戲團要來表演的消息。馬戲團展出一尾鯨魚(屍骸),一個(異國)王子,但來到的時候,人們發現鯨屍很臭,王子不斷延遲露面。外來的「福音」,以龐大身驅示現的改變象徵,很多書評人都視作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對後期資本主義降臨,所謂「歷史終結」的寫照。暴動燃點了,又一次破舊,但迎來的是更進一步、更深一層的抑壓和憂鬱。文本今天再閱依然耐看,處處找到當下的對應;歷史繼續重複,左推翻右,然後右又推翻左;左被詮釋為右,或異化為右,新左來革命,極右再回朝。人類總在重複錯誤,謊言揭穿了,換來只會是另一個謊言。
《反抗的憂鬱》比《殘缺的和聲》複雜的地方,是敘事者的多元(包括音樂家叔叔、他的夫人、電影主角和電影主角的母親……),但電影的編劇工作,同樣得到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積極參與,顯然後者也同意貝拉塔爾把主角收窄到智力最低下的送報生身上。無論我們把主角定位為見證一切發生的「白痴」或大智若愚的「時代人」,都會較易傾向覺得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和貝拉塔爾擁抱的世界似乎太悲觀了。
反抗,是為了拒絕權威,這個權威包括上帝,但沒有權威之後,反抗的人發現自己什麼也不是。天地不仁,不是我們想不想繼續向那個祂下跪,而是祂早主動離棄了我們。小說家筆下和電影導演鏡下的荒漠和類廢墟世界,既是反烏托邦想像,也是後現代心靈的倒映。虛無主義瀰漫,人際冷漠與體制暴力結合交織的,那無可避免的惡,席捲每一個角色,令他們在彷似停頓了的時空中,面對無盡的沒落與破壞,目睹自身的衰敗,逐步走向結束、死亡。
不過,真正懂得看的,不會因為這個「故事」世界感到絕望;恰好相反,會看到曙光才對。
真實而巨大的期許之流
法國思想家洪席耶(Jacques Ranciere)在其貝拉塔爾研究專著《貝拉塔爾——之後的時間》(Bela Tarr, the Time After ,2011,英譯本2013)便指出,貝拉塔爾的電影嚴格來說是沒有故事的。沒有故事,也就沒有接收中心(perceptive center)。導演創作的,是一大片寄託了期許的,連續的流(而長鏡頭有助流的湧動)。可以辨識的場景提供了讓觀眾進入,感受和體會的脈絡。這些場景儘可令人心灰意冷,貫穿其中的,那真實而巨大的期許之流才是關鍵。
洪席耶以《殘缺的和聲》的結局為例:表面上,主角被關進精神病院了,但過去一直被他照顧的,他的音樂家叔叔來探望他,並向他保證日後出院,他們會一起住,重建生活。角色倒轉了(被照顧者變成照顧者),但「即使宇宙毀掉,行星之間的關係尚存。也許這正是貝拉塔爾想說的,向我們保證他的電影是傳播希望訊息的。它們並非談及希望,它們就是希望。」(頁60-1)
是的,也許我們也要這樣看《都靈老馬》。電影的老馬來自德國哲學家尼采精神崩潰前抱其頭痛哭的那匹傳說之馬。尼采後來進了精神病院沒錯,電影以這個故事開頭,然後以對應上帝六日創造世界的滅世六天篇幅,描述人文的末日。某意義上,一如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其他文本,好像在引導觀眾/讀者預演了末日如何降臨一遍。如果說貝拉塔爾的電影沒有故事,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文本便是沒有角色的,因為他們都不需要了,他們多元發聲,滙合成一股大流,角色隨設定隨敘述而旋起旋滅。在末日早已降臨,其實不須演練的真實境遇中,由綿密長句承載的流才是重要的,而流正是帶我們克服所有表面悲觀和虛無的希望。
文˙朗天
編輯˙黃永亮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