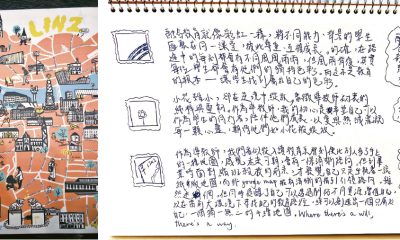副刊
{島嶼視角達人}潘律 從島嶼出發 發掘流動的連結與想像力

【明報專訊】理工大學紅磡灣校園裏,4月才遷入的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系,有一處走廊已被打理得別具氣息:一樽盛放熱帶植物的沃德玻璃箱,兩側貼滿大幅電影海報,看上去更像是獨立書店內的一方角落。這裏是副系主任、副教授潘律的辦公室門口,她的學術與影像創作的痕迹散落其中。從上海與柏林的都市空間,到70年代香港青年運動與亞洲藝術檔案,再到近5年的島嶼研究,她的學術軌迹像一張不斷延展、拼貼的流動地圖,圍繞着空間、視覺與記憶展開。與此並行的則是她10餘年的影像實踐:4部長短篇作品、數次駐留項目。研究與創作相互牽引,如同雙屏並置的錄像——互相呼應,又不依循規整的既定秩序。
關注「實在可見的空間」 跳躍地研究、創作
潘律最初接受的訓練集中在文學與語言學,之後在港大攻讀比較文學博士時,她形容自己「經過soul searching,突然之間不想再只是看文字」,成長在上海與柏林求學的雙重經驗,讓她愈發留意空間中的建築,及其收納的歷史記憶,逐步發覺自己真正想關注的是「實在可見的空間」。隨後,她以此為基礎拓展,由上海、柏林延伸至對東亞城市的視覺研究。進一步,當她選擇將香港作為研究場域,「做完所謂西方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突然覺得自己對亞洲鄰國的理解很淺」,於是再看到亞洲不同地方之間的關係。
入職理大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系,潘律置身一群紮實的歷史學家之間,來自比較文學的背景顯得「單打獨鬥」。歷史學者將檔案視為必須嚴肅對待且需基本訓練才能展開的研究對象,「我不排斥這種看法,也覺得檔案本身很有意思」。她便嘗試退一步問:「檔案是誰建的?裏面的材料又是如何被建構的?」一件物品一旦被收進「檔案庫」,就會呈現新的價值。以杜尚的《泉》(Fountain)類比,「原本只是尋常可見的瓷製小便池,移入展廳並簽上名,就成為20世紀最偉大的藝術作品之一了!檔案也是這樣一種視角和空間的轉換」。
隨後,她開始一場東亞跳島式的訪問——採訪各地的檔案建立者、學者、創作者、策展人,將這些對話於研究織成一本基於亞洲理論與經驗的書,串起香港、廣州、台南、新加坡、首爾、吉隆坡、東京、馬尼拉、新德里等地的實踐。這條路徑像魔法般時不時開出一個新入口,跳躍無定向,同時也啟發了潘律自己以學者的身分跨界影像創作。「我會常常思考,那我們每個人家裏的檔案是什麼?其實家庭錄像也是一種檔案的積累」。她便與日本導演荒木悠共同執導創作出《倒錯的編年史:出/入亞洲之旅》,將1960至1990年代東亞各地普通家庭拍攝的影像結合敘述拼合。混雜着英語、上海話、日語、閩南話,錄像機捕捉到看似庸常瑣碎的片刻,拷貝出處於私密空間中的記憶。同時,她嘗試將香港的空間與歷史作為影像創作主題,把研究觸及的檔案轉化為講述故事的素材,同藝術家搭檔王博合作了3部紀錄片:《隱形城市的踪跡:香港三記》(2016)、《瘴氣、植物、外銷畫》(2017)、《湧浪之間》(2018),新作《海島熱夢》將於今年12月首映。
以「島」思考香港歷史脈絡
看似跳躍的研究,其實一路未曾止步。近5年,潘律「跳」上了島。
今年9月,潘律在理大策劃了島嶼研究論壇《低潮高地:島嶼和活動影像在亞洲》。與會者的關注各有不同,有的着重於藝術創作,有的聚焦社區營造,也有人專注於歷史檔案的蒐集,彼此的思考不謀而合,呼應探索香港潮起潮落之間擱淺在灘塗上的問題。潘律解釋,島嶼研究的「跨界」並非突兀轉向,她始終的關心還是空間,而「重新發現香港空間」與香港整體公共空間的政治脈絡有關。她觀察到,2014年至2019年之間及之後的變化尤為鮮明——從前,本地政治公共空間幾乎全部集中在港島,其後,九龍與新界逐漸突顯。她的許多藝術家朋友因反高鐵等事件開始從事與土地相關的創作,空間的轉變帶來不少新的實踐與想像。
在這樣的脈絡中,島作為香港身分的這個意象又有棱有角地浮現了。「首先在地理上,它就是一個島,我們不能否認香港的這種地理的環境。再者,它還有第二層隱喻的作用……」潘律補充,「回過頭來看,香港全是島呀,原來大家並不會這樣想像香港,它常被視為都市空間,尤其是中環的CBD」。她指出,殖民歷史與都市化進程刻意進行了「去島化」,例如關於香港的視覺圖像,往往由港島山頂俯瞰維多利亞港,「是香港的整個殖民歷史賦予了山頂這個空間特別的價值」。
而在亞洲範圍內來連結島嶼,有機會奪回我們作為個體來認識這個區域的主導權。潘律的觀察延伸到其他區域:印尼作為「千島之國」,在殖民時期卻被荷蘭人強調土地本位(Land)與農業;香港則被強調都市的面向。於是,島嶼的視角淡出了記憶。「這個研究範疇,可以通過島重新去思考——這個區域的脈絡究竟是什麼?反思殖民地、民族國家所留下的那些人為的邊界,以及它們所建構的想像。」
策劃島嶼研究論壇 納入放映、落區
「每一個殖民架構都會打破原本的地理界線和定義,但島嶼本身始終有自己的脈絡。」潘律解釋,單從生態角度,洋流與氣候便帶動植物、技藝、故事與文化在島與島之間流動。她的一位學生研究海南黎族的黎錦,發現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紡織技術與東帝汶、越南之間有密切關聯,而這些線索往往因冷戰以來的國界劃分而被切斷。「我們會因地緣政治,幾乎忘記自己所在之地與海洋、與其他的島、其他的人之間的聯繫。」
構思這次的島嶼研究論壇,潘律不想停留在傳統意義上的學術會議,便跨界邀請不同文化背景的藝術家共同參與,並安排放映和落區。其中的協辦單位「島民」已策劃過2屆船到橋頭生活節,將香港4個離島區域的文化、藝術與社區串聯起來,這一次他們則邀請與會者走訪島上居民。潘律回憶,那戶家庭丈夫是古巴人,太太是香港人,都不是島上原居民,但長年生活於此,已融入島上社區。「島上門窗長年不關,鄰里之間互相幫助,關係非常密切。離島這樣的情境中,誰是華人、來自哪裏、是哪個族裔,並不在意『我是誰你是誰』這樣的強調。」
談到香港本土的這一概念論述,潘律一直覺得它是「蠻華人中心」的,「香港有非常重要的南亞裔的居民,如已經居住了超過三代以上的巴基斯坦裔、尼泊爾、印度裔,這些人不會被第一時間納入到本土想像中,納入到這個本土的話語裏面來」。相較之下,坪洲的實踐則「建構基於日常生活的local identity 」,不是口號或抽象概念。一位定居日本沖繩石垣島的藝術家也來參加島嶼研究會議,她在沖繩石垣島當地營辦駐留藝術家計劃,潘律之前拜訪時,對方召來朋友,其中既有日本本土(hondo,多指本州、四國、九州、北海道地區),也有來自不同國家,其後定居日本的居民。這種「歡迎大家從不同的地方來的『本土』,非本質性的本土,它不設限……我覺得之前讓我們覺得有點焦慮的本土,把那個界限設的很清楚」。
潘律補充了「島與島之間」(inter-island)的概念,島嶼本身便指向一種連結性(connectivity),但這種連結並非一旦建立便固定不變,而是始終處於流動之中。她形容:「今天我可能在這個島,明天又到了另一個島;我離開了,卻有新的人進來。」這種不斷流動、交替的往來和關係,是島嶼研究所關注的核心。
讓亞洲各地互相看見
那麼,這樣的視角下,究竟公眾可以如何理解什麼是島嶼要回應的問題?
「這種身分認同在全世界各地崛起的時候,我覺得島嶼是一個特別liberating的概念。」潘律又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最初關於島嶼的理論討論很多源自太平洋島嶼的經驗,學者Epeli Hauʻofa曾在We Are the Ocean中強調,這些散落海上的島嶼,並非孤立的點,而是一片「Sea of Islands」——是一個由航行、漁獵、親族往來和故事傳承連結起來的世界。從這個角度來看,海洋不是將島嶼隔開的界線,而是把島嶼彼此編織在一起的道路。潘律補充:「我一直覺得,亞洲與亞洲之間,在地理上非常接近;我們都有島嶼,也都有某種共同的被殖民經驗,或者共同承受過西方衝擊的經驗。但是,在研究和創作中,我們不斷去強調和西方的關係,卻很少追問我們自己與自己之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麼。」
因此,再回頭梳理她的許多跨界跳躍的作品與項目——無論是會議或放映的策劃,還是研究與創作,其實都是在嘗試建立離散中的連接,又於不被記憶的歷史中找到故事。「讓亞洲各地之間能夠互相看見:互相看見共同的創傷,互相看見未來可以一起走下去的可能性。在這樣的一個平台裏,過去與未來都能被重新發現。我覺得這挺重要的。」她還提到,有與會者講到solidarity(團結)的問題。「我認為這種solidarity曾經是活生生存在的,只是被某些東西切斷了。在這個時候,我會去想像這樣一種可能性:它的邊界是模糊的,是時隱時現的,就像潮漲潮退一般,有時清晰,有時不清晰……」
透過電影串聯創傷
潘律提到,自己在學術會議中嘗試把放映納入議程,帶來的反響亦頗有趣。她她舉例說,有一部極為重要但鮮少人看過的70年代日本電影Asia is One,片中訪談了日治時期的朝鮮人、沖繩人與台灣人,記錄他們在戰爭前後的經歷。「我覺得最震撼的是,它透過電影的形式,把過去與現在的創傷串聯起來,讓人看完之後完全overwhelmed(驚詫)。」她回憶,會後有部分學者及策展人直言深受震撼,並希望能在各自的地區再次放映。
記者追問,香港本地似乎很少有這樣的放映機會,「現在的狀况是兩個極端:要麼是走電影節,要麼是走地下放映。」她補充,香港國際電影節等本地藝文機構受框架限制,有時滯後於展映的趨勢,而學院的放映活動可能更有靈活性。「我這次選的香港片,在香港電影節完全沒有放過,反而是在北京或其他地方先行放映。比如小田香,我們請來的日本導演,他在日本非常重要,當下可以說是炙手可熱。」
文˙ 于惟嶼
{ 圖 } 黃志東、網上圖片
{ 美術 } 朱勁培
{ 編輯 } 梁曉菲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