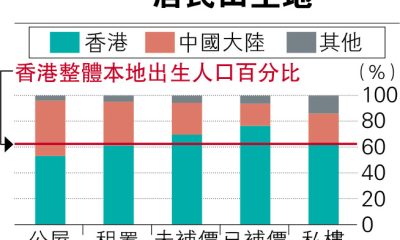觀點
阮穎嫻:重注創科經濟將香港帶往何處?

【明報文章】去年施政報告發表以來,我曾評論其中多項政策方向,尤其聚焦經濟發展與科技創新(包括2023月6月6日《從創科沙漠到創科中心》,2025年6月10日《產業政策的兩面刃》),但其後實施成效值得審視。今年施政報告於9月18日發表,有很大部分跟去年一樣,好聽就叫延續去年基調,唔好聽就是換湯不換藥,毫無新意,因此無必要篇幅冗長,害官員議員在宣讀時瞌眼瞓。
今年,施政報告仍把發展定為核心目標,依然以推動經濟發展、吸引人才及擴大市場為主要方向,這一點與去年並無根本改變。這反映香港在後疫情時代重啟經濟、強化競爭力的急迫需求。
融資開發新區 需提令人信服藍圖
現在開發新區最大問題是無錢。「明日大嶼」才剛剛正式宣告「玩完」,係好事。政府赤字連年,盈餘萎縮,並無財力同時開發北部都會區和明日大嶼。北部都會區背後是促進深港同城化,融合大灣區的國家大方針。明日大嶼只是前朝林鄭月娥提出的計劃,現在人走茶涼,應該擱置。已花出去環評的錢,是沉沒成本(sunk cost),無可奈何。明日大嶼不應上馬,早聽我講,政府可以省下更多錢。
問題是政府財赤會否嚴重到連北部都會區都無錢發展。有說政府連基建都無錢興建,所以想用「片區開發模式」,要發展商投地之餘幫忙發展基建。但香港住宅價格已連跌3年,累計跌三成,商業地和商舖跌得更多,因此發展商自己都無錢,個個負債纍纍,未必有資源參與片區開發。二三線發展商要承擔這麼大型的發展當然吃不消,大發展商亦不看好前景,並有資金流問題。唯一有錢的發展商已經被嚇跑,運河一役弄得焦頭爛額,裏外不是人,恐怕沒有意欲發展北部都會區。
發展商要計一條投資回報的數,買地起樓預期回報要夠高才有經濟誘因令私人發展商參與。有來自中國內地的經濟學家告訴我,雖然北部都會區吹到如火如荼,但國策是大灣區融合,最後兩地的樓價融合到一樣,那北部都會區的地究竟值幾錢?為什麼有人會用現今香港價錢買樓及買地?內地經濟學家說,有錢不如去買深圳河以北現時低水的房地產。
政府打算以基建債、公私合作模式 (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民間興建營運後轉移模式(Build-operate-transfer,BOT)、設立新公司等方式分攤資金與風險。但無論如何融資,最後是否能收到回報,政府需要提出令人信服的藍圖。綜觀近期內地政府牽頭發展的雄安新區和前海等,都有點雷聲大雨點小。
產業園發展不能只靠土地
北都要發展成科技中心,鄰近深圳;深圳是中國創科中心,在深圳旁邊發展一個區,依仗它的外溢效應,可能成功率較高。那就要看在制度、配套上是否能吸引更多香港境內生意。對於深圳政府來說,肥水當然不流別人田。香港從來不是創科中心,環球科技業者首選是美國,然後是新加坡,再來才可能是香港。其他競爭者包括有迪拜及其他中國城市如北京、深圳、上海。所以香港是創科人才最少第三手選擇。
如何利用香港優勢,把創科產業及人才引進才是真正挑戰。產業園發展不能只靠土地,應以供應鏈為單位,精準招攬企業。針對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新能源等重點產業,繪製完整的產業鏈圖譜。先確定幾家核心企業,再透過專業服務和測試場景擴大生態圈。人流、物流和數據流需同步規劃,解決簽證、住屋、跨境運輸和數據交換等障礙,避免資源無法流動。
政府可將知識產權交易、國際仲裁、標準認證等高增值服務納入園區,加強香港優勢,避免與深圳等地競爭。考核官員應聚焦有效就業、人均產出和高收入,而不是單單窮盡資源「起到出嚟當贏」(或當達成KPI)。施政報告雖強調創新及基建,但缺乏提升中小企生產力和改善營商環境的根本改革,令人擔憂發展動力的持續性。
報告強調與內地的多方面連接,如金融互通、北部都會區、人才與教育合作,力求成為「超級連接器」。然而,香港能否憑此打造跨境金融創新中心或企業總部基地,仍需更具體的制度創新及流程簡化。現階段兩地產業結構、監管和人才融合仍有磨合,跨境合作基礎仍未穩固。
北部都會區的發展不容有失。由於投資巨大,若無回報,必然對政府整體財務穩健構成壓力,最後難免影響民生社福等開支。影響到褔利,已經不止是納稅人的事,而是全香港人之事。因此,除了加速興建,跨境協同、制度、法規等更需要關注。
工程「開數」需清楚交代
另外,施政報告第240項「支援中小企」,第(iii)項稱,「政府原訂未來五年的基本工程開支每年平均約為1200億元,為支持本地建造業,我們會額外預留300億元在未來兩至三年加大工程項目開支,以持續推動經濟發展」。現在的工程項目愈來愈多由非本地建造商承辦,本地建造商例如80年老牌建商保華清盤收場。建造業因為外勞問題,有本地工人投訴無工開。在輸入外勞一事上,政府需平衡各方利益。尤其是非本地勞工在香港搵錢,但會將一部分的錢匯離香港。由於這些錢沒有投入到本地經濟,沒有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造成漏損(leakage),間接影響香港的生產總值。
此外,300億用來做什麼工程,施政報告沒有說明。本身每年1200億基建已經相當高昂,300億不是小數目,沒有指定用途非常不尋常。用來做什麼工程,政府需要向納稅人交代。公營機構及法定機構,每每開數,要寫得很清楚。我去學術會議,報銷公共交通費用,區區73港元,都會被問及是搭何種公共交通,然後還要解釋是機場快線加了價。慳慳埋埋,濕濕碎碎,幾廿蚊都問長問短,幾個部門來來回回,連行政成本都蝕埋。現在300億話走就走。
帳目不清是發展中經濟體的常見弊病。當一些款項沒有指定用途,任由官員配置,容易造成貪污腐化。常見例子如尋租行為,政府的標都給了自己人,大家努力攀附,不事生產。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者Daron Acemoglu,亦有講過掠奪式制度的問題,令很多國家不能發展。究竟香港會繼續向這個方向行去,還是可以取道包容式制度,讓大家分享經濟發展成果,這才是香港經濟是否能長遠發展的關鍵。
作者是香港大學經管學院講師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阮穎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