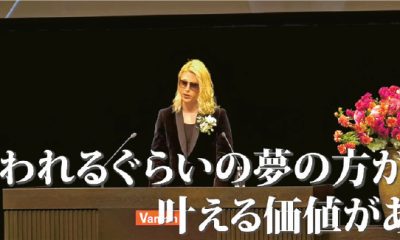副刊
【香港】performing——17/24

【明報專訊】在河原溫的展覽打轉時,身邊跟着一女和一女,應是策展團隊和來賓,她向她介紹,這是他的時間,這是他的檔案,熱中而溫馴。我參透不能,聽方微微頷首臉無表情到底是什麼意思。她明白?她懂?假如,當代藝術機構認定觀眾須透過扮演來了解作品(扮徐冰,用毛筆和水寫習字帖;扮畢加索,於數碼屏幕上塗塗畫畫),行為藝術也應如此。就着時間,就着存在,我決定扮謝德慶的《一年行為表演1980-1981》。將一年截短至一日,取鐘面的數字間距為單位,定規則:我和H,二人在房間24小時,隔5分鐘合照一次,讓一格菲林藏起我們的40分鐘,讓一筒36幀菲林曝光共288次;二人主要活動範圍為牀,聊天紙筆允許,煮食梳洗如廁允許,凌晨時分播電台節目允許,其餘不允許。
我的這種「回應」,以體驗為宗,無意嚴格模仿,大概是鬼打牆式對話,在已有的軌上放任脫軌。先說表演結果:二十四分之十七小時成功,之外,因一方勞累睡着而無法拍攝。「出乎意料,我無法感受時間的流動,那24小時,從日常之中被抽離、凝視,成了一磚很奇怪的物體。」「5分鐘實在碎片,無法完成任何事,我本來想像不停不停聊天,結果都是沒話題的閒談,無法回想,失憶了一樣。」「對,像吃飽了沒之類。但我的感受很強烈,你有沒有?」「整體平淡,你是指?」「完結那一刻,我有種強烈的矛盾的喜悅,我想啊謝德慶應感受到同樣的,近乎狂喜,一切非必要,一切乃人的自由選擇與遵從,所以延衍美。」我們就在裏頭,他揑着剛冲好的濕漉漉菲林條,開玩笑,說。我看着,忽然發覺,過去從不存在,影像並非記錄,卻為創造,把當刻即逝的「時間」重新造出來。(為何一人變二人?我的天馬行空是:人每天睡覺,人與人幾乎從沒醒着共度24小時,若然,若能,可否抵達一種極端的親密感?但,頭昏昏,無相關感受。無相干,實驗放任脫軌。)
小結:體驗到行為藝術以「活着」為媒材所需的驚人體力和意志,如我頭一兩小時開始渙散,有嘔吐感,H說燈關了就欲睡;也更明白藝術「使某物可被觀看」的割離性,比起謝德慶活生完成的一個個計劃,河原溫自某時間點起拒絕被他者記錄,將凝看的權力拉延至自己經已消失的世世代代,原來是在重建以一整生命為本的巨大「過去」。
文:吳騫桐
(寫字的人當藝術行政)
IG@odeng____
[開眼 大都會文藝誌]
日報新聞-相關報道:
【倫敦】Camden Art Centre:倫敦最貼地的藝術中心 (2025-08-01)
【東京】自己做 (2025-08-01)
【紐約】申請100次 (2025-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