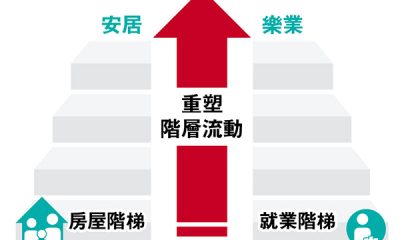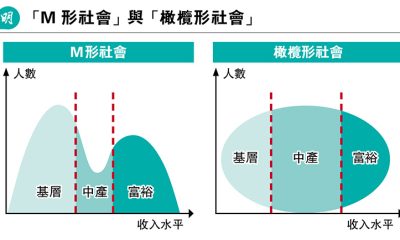觀點
洪雯:需求驅動vs.願景驅動(十一):北都建設必須「抓大放小」

【明報文章】本系列文章探討需求驅動與願景驅動這兩種發展模式。前幾篇回顧玫瑰園計劃的建設歷程,正是因為玫瑰園計劃超越了香港一貫以來的需求驅動城市發展模式,是一個以未來為導向、將願景驅動與需求驅動相結合的雙輪驅動發展模式,其成功落實的經驗,值得總結和參考。
2021年政府提出發展北部都會區,作為落實「北創科」這一願景的主導區域。我認為,北都堪比一個「升級版」的玫瑰園計劃。
北都是「升級版」玫瑰園計劃
玫瑰園計劃的願景,是能夠清晰描繪的物質環境(physical environment),建成後市民看得見、摸得着。正如1989年施政報告「展望將來」部分的一句話:「我們清楚知道要建設的目標。」
相比之下,北都發展既涉及基建建設和土地開發,更包括新興產業培育和香港經濟結構的轉變。前者是硬件設施,建成之後看得見、摸得着,但這只是第一步;後者則是在硬件載體之上的產業發展和培育,是「北創科」的真正目標。而這些「軟件」,我們目前尚難以清晰預見。
可見,北都之願景,是一個結合硬件和軟件的綜合都會區發展,涉及範疇和複雜程度遠超玫瑰園計劃。即便是在基建建設和土地開發方面,北都總面積達300平方公里,佔本港面積約三分之一,涉及多個新發展區和多項大型工程建設,規模上亦遠超玫瑰園計劃,堪稱「升級版」的玫瑰園計劃。
不過,硬件是基礎和載體,是「北創科」必須邁出的第一步。2022年政府提到落實「基建先行,創造容量」理念,陸續為北都規劃了一系列交通基建,包括港深西部鐵路、北都公路、北環線、新界東北線等,並陸續完成了4個功能區(包括高端專業服務和物流樞紐、創新科技地帶、口岸商貿及產業區、藍綠康樂旅遊生態圈)當中前3個區的規劃工作。
不過,北都提出至今已近4年,尚未真正起步。比如上述北都的交通路線中,除了早於2014年就落實興建的北環線第一階段有望在2027年通車之外,其他工程至今全部尚在很初期的階段,建成時間均指向10年之後甚至更長。
土地供給方面,未來5年預計產出約570公頃熟地。聽起來不少,但仔細看便發現,這些熟地主要來自古洞北/粉嶺北、洪水橋/厦村,以及元朗南,均是上世紀末就提出的新發展區,最遲開始規劃的元朗南也已經有十幾年歷史。而科技用地主要集中於新田科技城,該區的規劃程序去年才完成;未來兩年可以招商入駐的,就只有河套即將營運的3棟樓和預計2027年完成的另外5棟樓。如今國際局勢風雲巨變、科技加速迭代、顛覆性的創新不斷湧現,「北創科」的發展還等得起嗎?
於願景驅動模式下,願景能否實現並不確定,因此早期投資風險很大,需要政府在決策上高瞻遠矚的決斷力、高效而精準的貫徹執行力,及動員社會參與的廣泛引導力。這是願景驅動模式給政府提出的挑戰。
玫瑰園計劃的落實,讓我們看到當時政府在這三方面的能力。而回歸之後,香港逐步放棄了願景驅動發展模式,全面轉向需求驅動模式。背後原因,既有「積極不干預」的管治傳統,更因港英時期培植起來的反對勢力於回歸後逐漸取得大量政治資源,並成長起來,對特區政府施政施以變本加厲的阻撓和無所不用其極的破壞。
從「抓大放小」變成「抓小放大」
這樣的政治環境,使政府處於相對弱勢,處處受牽制;大事小事均被高度政治化,官員動輒得咎,出現所謂「官不聊生」惡劣環境,官員和公務員逐漸產生怕做事、怕風險、怕擔責的文化和心態。政府無力果斷決策,亦欠缺強勁執行力和廣泛的社會影響力,以致發展上陷入「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困境。即便政府提出某些願景,也因反對勢力阻撓而無法推行。只有需求驅動的發展模式,即眼前有實實在在、可預計的需求作為支撐,有關決策才可能推行下去。
正是這樣的背景下,政府管治模式從玫瑰園計劃時期的「抓大放小」,變成後來的「抓小放大」——大的、有風險的決策,政府無力決定、推行,便逐漸放棄(比如《長遠房屋策略》就放棄了提升居民自置居所比例的願景);反而,各部門為了確保自己不犯錯、零風險,僵化甚至荒謬地「按本子做事」,緊緊抓住各種小細節,重重監管、層層審批、種種限制,緊緊咬住絲毫不放鬆。而項目能否推進、成本多少,這些大問題卻根本不在考慮範圍。天價工程不斷出現,延時、超支成為常態,很多創意和發展機遇被扼殺在繁複冗長的行政監管中,發展速度早已追不上世界創新步伐。
這種「抓小放大」現象,不僅僅出現在工程發展中,還反映於香港社會管治的方方面面。比如早前香港提出發展「夜經濟」;可是,要在香港擺一個夜市的小攤實非易事。食環、城規、消防等各種牌照及許可證審批過程之複雜和冗長、限制之多,令人吃驚。即便是我們大力發展的創科產業,也有層層障礙要突破。比如,晶片製造過程中有不少環節要經過環保和消防的冗長審批,沒有特殊安排,走正常渠道,不知要歷時多長;建築工程採用組裝合成法(MiC),有關部件的運輸和倉儲過程,也受到很多複雜規限,成本因此增加。
我聽到不少年輕創業者反饋:香港創業成本實在太高,辦公室場所和人力資源昂貴自然不必講,但尚有其他成本包括複雜監管、冗長程序、各類表格,還有監管者僵化甚至荒謬地守着部門規則寸步不讓,力保自己無過失。
陷入微細監管 如何重拾活力
這樣的營商環境,小企業、小創業者怎麼能夠成長起來?我來香港的這20多年,沒有見到一間本地的新企業成長成為有國際影響力的大企業;今日所見的大港企,都是幾十年前成立的了。我們今日所有的新市鎮,都是回歸之前建成或規劃好;而如今納入北都範圍的幾個新發展區,經歷十幾廿年,離成形還有不少距離。香港如果不抓大事,反而陷在微細監管(micromanagement)的死胡同裏不走出來,如何能夠重拾發展活力?
慶幸的是,今日的香港已邁出內部政治鬥爭的泥沼。因中央的果斷行動、撥亂反正,「愛國者治港」原則終於得到落實;長久以來阻擋和破壞香港發展的大政治問題,已大體得到解決。香港是時候回應各界對改革和發展的期待,將願景驅動與需求驅動發展模式相結合,在管治中抓大放小,為北都發展提速、提效。
作者是立法會議員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洪雯]